图|海丝泉州文旅之声 ©
物道君语:
花与青丝相遇,织就跨越千年的浪漫。
簪花,簪住的是四时芳菲,更是我们对生活最温柔的反抗。
冬天,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
十一月的寒风颇有锋芒,看路上那些光秃的枝桠,让人格外怀念那些繁花似锦的日子。
说到繁花,物道君便想起今年9月在泉州看到的“簪花”。
回溯历史,从汉代的重阳茱萸“菊花簪”,到唐代《簪花仕女图》中的“荷花簪”,到宋代的“不分男女满城花事”,再到今日泉州蟳埔女的“头上花园”。
原来,国人早已将花的魂魄,簪进了自己的生命里。
我们对美的执着,从未因朝代更迭、四季轮回而断绝。
但簪花,真的只是一种美丽的头饰吗?
物道君认为,簪花里蕴藏着生命的哲学。
图|泉州文旅 ©
虽说中国人是最擅长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意的,但史上最痴迷簪花的,竟是宋代的文人墨客。
宋代皇帝因郊祀等活动出行归来时,仪仗队伍中的男性大臣们都要簪花。
杨万里曾在《德寿宫庆寿口号》描绘道:
“春色何须羯鼓催?君王元日领春回。牡丹芍药蔷薇朵,都向千官帽上开。”
每逢重大典礼,从皇帝到百官,人人帽上簪花,远远望去如一片流动的花海。
男子簪花,不是阴柔,是庄重与风雅的完美融合,是一种超越性别的审美自信——美,从来不该被定义。
真正的风骨,在于有勇气定义并拥抱属于自己的美。
去过泉州蟳埔村的朋友,一定都被那里的阿姨震撼到。
她们身着大裾衫,头发梳成圆髻,横插一根象牙筷,然后将一串串玉兰、素馨、茉莉等鲜花簪成一个硕大的花环。
泉州蟳埔女每日凌晨出海,黄昏归航,在牡蛎壳垒成的蚵壳厝间穿梭。
发髻上的鲜花,与生活的粗粝形成奇妙的对照。
海风咸涩,却吹不散她们发间的芬芳。
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里写道:
“春夏秋冬,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,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。风霜雨雪,受得住的就过去了,受不住的,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。”
而蟳埔女选择用满头繁花,来对抗生活里的风浪。
她们相信:“只要头上还有花,日子就可以甜一点。”
这种朴素的生命智慧,比任何哲学都更动人。
图|陳陳趣旅行 ©
你可知:蟳埔女常簪戴的茉莉、水仙、素馨花,竟都是外来品种,原产自印度及波斯?
这些如今寻常的花卉,都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。
宋元时期的泉州,阿拉伯商人不仅带来了异域商品,更赠予当地人奇花异草。
于是,中东的素馨与东方的发髻相遇,才成就了一段文明交融的佳话。
这也印证了鲁迅所倡导的“拿来主义”智慧:
“我们要运用脑髓,放出眼光,自己来拿!”
面对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芬芳,先人们没有排斥,而是欣喜地将其“拿来”,编织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审美体系中。
这种自信与包容,让簪花这一风俗,超越了地域,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见证。
簪花文化既有本土的深沉,又拥抱外来的鲜妍。
现在我们看到的满头发花,何尝不是古代中国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?
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与融合,和而不同,方能美美与共。
图|海丝泉州文旅之声 ©
今日的蟳埔村,每天有成千的游客前来体验簪花。
“60元服装妆造全包”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年轻的女孩们顶着华丽的簪花围,于古老的蚵壳厝前拍照。
这热闹非凡的场面,却让一些传承人忧心——
塑料花替代了鲜花,传统的文化语境被简化成打卡背景。
想起木心的诗句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,马,邮件都慢。”
而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,快到来不及品味一朵花开的过程。
但转念一想,何必苛责?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方式。
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中写道:“世间万物皆有情,难得最是心从容。”
重要的是,在这些喧嚣的体验中,总有人会停下脚步,去倾听花朵背后的故事。我想:不妨先让花戴在头上,文化自然会住进心里。
图|海丝泉州文旅之声 ©
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,一定有一个小小花园。
它可能藏在宋人簪上的牡丹里,藏在蟳埔女发间的素馨里,也藏在你我面对生活时那份不肯妥协的爱美之心裡。
为自己簪一朵花吧。
不必繁复,哪怕只是一小枝腊梅。
当花香掠过鼻尖时,你会听见一个古老民族最温柔的告白:
生活或许艰难,但美,触手可及。
“今生簪花,世世漂亮。”这不仅是一个祈愿,也是一种决定——
在任何境遇里,我都要活出一朵花的姿态。
图|海丝泉州文旅之声 ©
大家有体验过非遗“簪花”吗?
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、晒图,分享你最美的人生簪花照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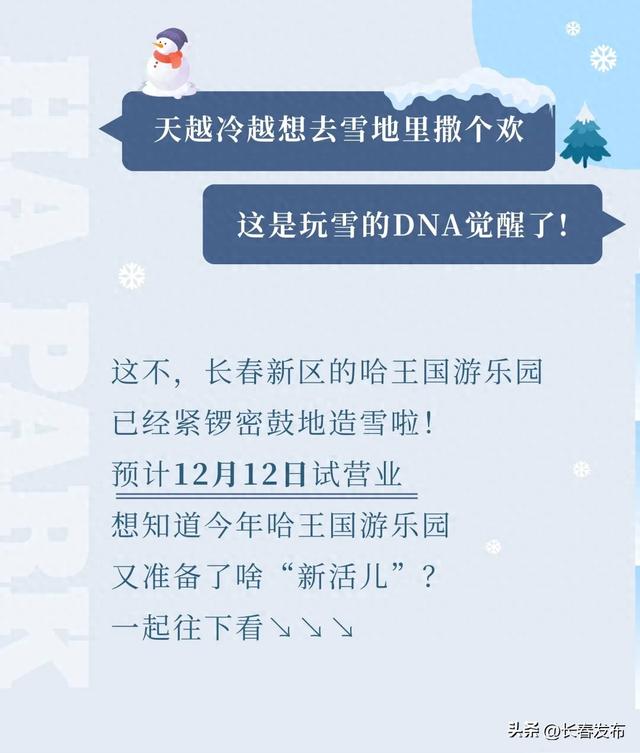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