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水调歌头·重登石室岩
久别石室路,重踏赤天阶。
卅年尘外心契,犹与此山偕。
千级青阶盘翠,一渠清波绕岫,云白衬天开。
汗透轻衫湿,蝉语入松钗。
登楼望,凭栏想,意悠哉。
亭名未解深意,风自送风来。
莫道峰高路陡,且惜阶前光影,步步印苍苔。
鬓角霜丝在,心向最高台。

暑阶寻幽,山与岁月皆旧识
“久别石室路,重踏赤天阶”。2025年8月11日,上午,末伏的热浪还未褪去,我已站在石室岩的山脚下。
说是“久别”,其实不过是去年盛夏一别;但石阶被烈日晒得发烫,脚踩上去果然有“赤天”之感,这滚烫的触感,倒与年年登山的记忆重合——原来有些牵挂,从不会因时光稀释。

“卅年尘外心契,犹与此山偕”。退休近五年,这座海拔347米的山成了我最忠实的“体检官”。不必说尘世烦忧,只需站在山门处望一眼青黛色的山影,便觉心神安定。

山从不言语,却懂我每一次来此的用意:不是征服,而是对话,是与岁月、与自己的默默约定。
“千级青阶盘翠,一渠清波绕岫,云白衬天开”。新修缮的石板路在绿树间蜿蜒,1589级台阶像串起时光的珠链,一级级通向云端。

山脚下,东圳水库的水渠如碧玉带绕山而行,偶尔有微风裹挟水汽拂过,给34℃的高温降了温。山腰间,抬头是水洗过的蓝天白云,低头是浓荫蔽日的绿意,蝉鸣在叶间此起彼伏,天地开阔得让人心头发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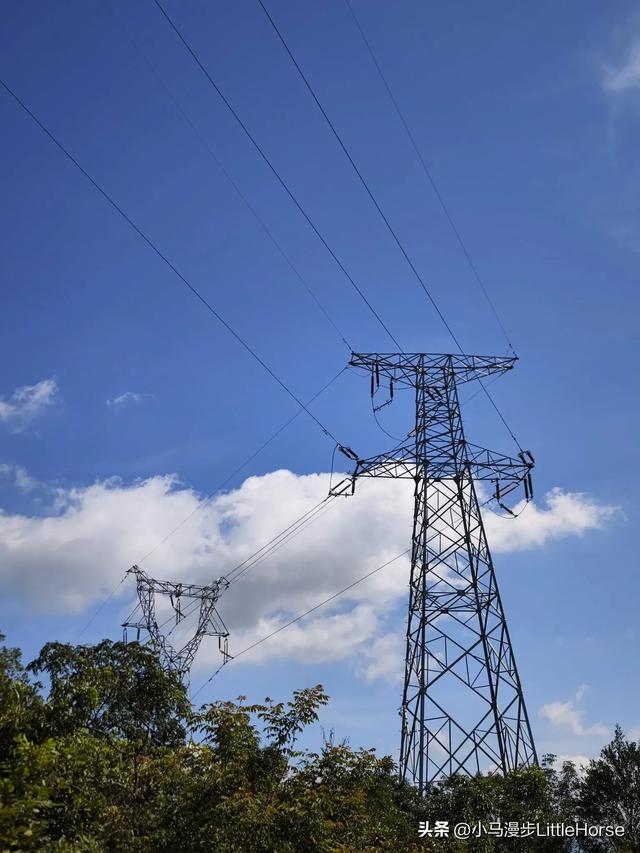
“汗透轻衫湿,蝉语入松钗”。天气炎热,没走多久,汗水已浸透短衫,贴在背上微微发黏。但这燥热里藏着生机:松针如钗般细密,蝉鸣声从枝叶间隙钻出来,清脆得像要把暑气都震散。停下擦汗时,竟觉得这汗水与蝉鸣,都是山对登山者的馈赠——痛快淋漓,才是盛夏登山的真味。

登高悟理,风与初心皆自在
“登楼望,凭栏想,意悠哉”,行至半山的双子亭,终于能歇脚远眺。扶着栏杆望去,莆阳全景铺展在眼前:兰水如带穿城而过,高楼与旧巷交织,远处的壶公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山风忽然穿亭而过,吹得额前碎发轻扬,刚才攀登的疲惫仿佛被这风卷走,只剩下满心的舒展与惬意。

“亭名未解深意,风自送风来”。山路愈陡,思绪也愈发轻盈。转过石岩寺的石砖塔,看到“乘风亭”的匾额时,忍不住笑——这里明明无风,反倒是刚才的双子亭凉风习习。
到了“楼心亭”又犯迷糊:这般能让人静心歇脚的地方,为何不叫“栖心亭”?正琢磨着,一阵清风忽然拂过,才恍然大悟:山风从不在意亭名,它想吹就吹,正如人生的答案,往往藏在不经意的瞬间。

“莫道峰高路陡,且惜阶前光影,步步印苍苔”。中途见有年轻人望着陡峭的石阶犹豫,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总说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攀登”。

如今才懂,登山的意义从不在“登顶”二字,而在每一步的踏实:阳光透过树叶在石阶上洒下斑驳光影,青苔在石缝间悄悄生长,每一步落下,都是与山的温柔触碰。
“鬓角霜丝在,心向最高台”。终于抵达最高处的望山阁,虽因树荫遮挡没能看清远处的壶公山,但站在这里时,心里却格外敞亮。

鬓角的白发早已藏不住岁月的痕迹,但望着脚下蜿蜒的石阶,想着刚才遇到的每一个向上攀登的身影,突然明白:年龄从不是限制,只要心里装着“最高台”,每一步都能走出向上的力量。

一阕词,一条路,一颗心
今天登山,写一篇《水调歌头·重登石室岩》。我想,以词为骨,以景为肉,以情为魂,将登山的寻常体验,力求写出岁月的厚度与哲思的深度。

开篇,我以《水调歌头》定调,随后循着词的上下阕语序展开,词中“赤天阶”“清波绕岫”“苍苔”等意象,都在游记中得到细腻还原,实现了“词为纲、记为目”的巧妙融合。

文中,我没有刻意拔高的“励志”口号,却在细节中藏着动人的力量:被晒烫的石阶、浸透的衣衫、蝉鸣与松钗的呼应,让登山的体感真实可触;而对两处亭名的疑惑、对“最高台”的执着,则将叙事升华为对人生的感悟——正如词中所言,“步步印苍苔”的踏实,远比“登顶”的虚名更重要。

全文,字里行间透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岁月的坦然,山是风景,是伙伴,更是镜子,照见“鬓角霜丝”下那颗依然“向高台”的初心。
一阕词,一条路,一颗心。今日,我重登石室岩,既见山之青幽,更见心之赤诚,体验一下“以词记游,以游悟词”的妙处。

景语含情,岁月与山俱老。情语入理,初心与风同来。我想以山为镜,以步为诗,将“检验体力与毅力”的寻常事,写成“岁月与初心对话”的深情篇。
山,还是那座山,路,还是那条路,但岁岁登临时,老去的是鬓角霜丝,不老的是“心向最高台”的赤诚——这便是人生最美的“登高”。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