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企融合 美美与共

古都春色风情
我在西安已经四十多年了,我非常喜欢十三朝古都,这里的文化底蕴非常雄厚,这里的风景也日益增多,每天都是忙忙碌碌,每天都是诗情画意,每天都是撰写相关,我喜欢特色西安!
春,又一次在钟楼的屋脊上踮起脚尖。
四十五载了,我目睹它从汉瓦的缝隙里探身,在唐砖的苔痕上落脚;目睹它把大明宫含元殿的残影轻轻抹平,又将兴庆宫沉香亭的霓裳重新裁出。它像一位不老的说书人,年年带着同一册竹简,却每次都能翻出新章。
今年的春,比往年更早,也比往年更慢:早在一月未尽,护城河畔的柳丝已洇出青烟;慢在每一朵花都不肯仓促,仿佛要把十三朝的呼吸一次吐纳干净。我站在永宁门城墙根,仰头望见一只灰喜鹊掠过垛口,翅尖划破了薄金色的晨雾——那一刻,我知道,长安的春,又正式开场了。
长安的风,是青铜器里逃出的绿锈,带着周礼的余温,带着秦俑的冷峻。它掠过书院门古槐,卷起碑林拓片的墨香;掠过曲江池新荷,卷起霓裳羽衣的丝弦。风里还有羊肉泡的孜然、甑糕的蜜意、冰峰汽水的橙花,以及我案头旧稿上淡淡的樟脑味。
风最懂分寸:吹不翻含光门下的老妪的竹篮,却能吹散她额前白发里的雪;吹不动碑林石经上最深的凿痕,却能吹活石缝里一茎野薄荷的脉搏。
水
八水绕长安,春来时,泾渭先醒。
渭河的水像一条刚拆封的宣纸,被夕阳轻轻洇开,边缘泛着毛茸茸的光。灞桥的柳,把倒影折进水里,折成一把柔软的折扇;扇骨是柳枝,扇面是粼粼金波。
昆明池的水更静,静得能照见两千年前李夫人的眉黛。水鸟贴着镜面掠过,羽翼沾了水气,抖一抖,便抖落半池星子。
尘
尘是长安最轻的史书。
它落在明城墙上,是秦砖的粉末;落在钟楼上,是唐铜的绿屑;落在小雁塔檐角,是宋瓷的冰裂纹。春日的尘,被雨水一浇,便成了泥,成了可以发芽的泥。
我常在南门外的下马陵,掬一捧带尘的土,指缝里漏下的不是沙,是周秦的铜车马、汉唐的瓦当、明清的砖雕。
长安的春,始于一场杏白。
青龙寺的樱花尚未舒展,小雁塔后坡的杏花已先声夺人。它们像一群穿素衣的宫女,提着裙摆,从唐代的壁画里径直走到我的镜头里。
杏白是冷白,带着一点月光的瓷感。花瓣薄得几乎透明,却能托住一整座长安的重量——大雁塔的塔影、兴庆宫的箫声、甚至我四十年里所有未写完的诗。
桃红
紧接着是桃红,从樊川到少陵原,一路烧过去。
桃红是长安最艳的胭脂,它把汉代的铜镜、唐代的鎏金、宋代的缂丝,统统染成同一种颜色。
我在桃林深处,看见一位穿汉服的姑娘,发间插着鎏金银簪,簪头垂下一粒珍珠,与桃花瓣一起晃啊晃。她低头嗅花,我低头嗅她发间的唐朝。
榴红
榴红来得最晚,也最沉。
它不像桃红那样轻浮,它要压得住枝头,也要压得住历史。
长安的石榴,多植于寺院——大慈恩寺、大兴善寺、罔极寺。榴花一开,整座寺院就成了炼丹炉,把晨钟暮鼓、梵唱经声,都炼成一粒粒朱砂。
我偏爱大兴善寺的石榴。寺里僧人说,那几株是唐代的遗种。我信。因为每朵花里,都住着一个穿朱红袈裟的玄奘,正用梵语诵经。
钟声
长安的钟声,是春的心脏。
钟楼的大钟,敲一下,长安就少一秒旧时光,多一秒新绿。
小雁塔的钟声,敲一下,雁塔晨钟的碑拓就淡一层墨,多一层苔。
我习惯在清晨六点,站在钟楼地下通道的入口,听钟声穿过车流人潮,像一条金色的河,漫过我的脚踝。那一刻,我确信自己仍活在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的韵脚里。
鸽哨
鸽哨是长安春日的笛子。
一群灰鸽从南门箭楼起飞,哨音划破蓝天,像一支无形的笔,在天空写下“长安”二字。
那声音让我想起父亲。四十年前,他骑自行车载我路过南门,头顶掠过一群鸽,他说:“听见没?这是唐朝的鸽哨。”我那时不懂,如今懂了:鸽哨里藏着一座城的回声。
秦腔
秦腔是长安春日的鼓。
它不在剧场,在环城公园的树荫下,在德福巷的茶馆里,在八仙庵的庙会中。
老艺人一嗓子“三滴血”,唱得牡丹开了第二茬。
我蹲在环城公园的围栏外,看一位白发老者唱《斩单童》,他青筋暴起的手敲着檀板,每一下都像敲在我心口。唱到“儿啊——”时,一片柳絮恰好落在他肩头,像戏服上突然多出的水袖。
四月底,长安的槐树开始泄密。
一串串白槐花,像微型佛塔,挂在枝头。
老婆提着竹篮,带我摘槐花。
回去做麦饭:槐花拌面粉,蒸十分钟,浇蒜泥辣子油。
一口下去,满嘴是春。
年年岁岁,槐花依旧。我在朋友圈晒图,配文:“这是长安的春,长在舌尖上的舍利。”
琼锅糖
琼锅糖是长安春日的琥珀。
它把麦芽糖、芝麻、核桃熬成一块,敲碎时,声音像春雷。
我从回民街买回一包,用麻纸包着,纸上的油渍像地图。
我舍不得吃,每天舔一小口。
如今我买来给儿子,他咬一口,说:“爸爸,这里面有股太阳味。”
我点头。那是长安的太阳,晒了四千年的太阳。
卖风筝的人
每年三月,大雁塔北广场总有一位卖风筝的老人。
他的风筝不是塑料布,是宣纸和竹篾,画着玄鸟、夔龙、飞天。
我问他:“您这风筝能飞多高?”
他答:“能飞进王维的诗里。”
我买了一只“玄鸟”,在广场放飞。风筝越飞越高,像要驮走整个大唐。
穿汉服的姑娘
大唐不夜城的步行街上,穿汉服的姑娘比游客还多。
她们提着灯笼,裙摆扫过地砖,扫出一片月光。
我偷拍一位姑娘,她回头笑:“叔叔,拍好看点,我要发给李白看。”
我大笑。长安的春,连玩笑都带着诗意。
拾荒的诗人
环城公园里,有一位拾荒者,每天背蛇皮袋捡瓶子,这就是我,囊中羞涩,口袋比脸还干净。
我捡完一通瓶子,坐在长椅上,用圆珠笔在烟盒上写诗。
我写的是:“柳絮是春天的骨灰/我把它撒进渭河/让唐朝的鱼/再死一次。”
我口袋里的零钱就剩几个硬币了。我仍然说:“我要去买纸,还有笔。”
我掏出笔记本首先是写“谢谢你,长安。”
碑林的春,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。
《石台孝经》的碑侧,冒出一丛野薄荷,香气像唐玄宗的叹息。
《颜勤礼碑》的裂缝里,栖着一只七星瓢虫,背上的斑点像颜真卿的墨迹。
我抚摸碑面,指尖沾了一层青苔。那是时间最轻的包浆。
城墙
城墙的春,是从箭孔里漏出来的。
我租自行车绕城墙一周,花了两小时十三分,骑的很慢。
骑到含光门段,看见一位父亲把孩子举高,让他摸箭孔。
孩子说:“爸爸,这里面有风。”
父亲答:“这是唐朝的风。”
我差点落泪。
大明宫
大明宫的春,是从废墟里站起来的。
含元殿的台基上,开着一片二月兰。
我躺在台基中央,闭眼听风。
风里有丹凤门的鼓角,有宣政门的莺啼,有紫宸宫的环佩。
睁眼时,一只白鹭掠过遗址,像从《步辇图》里飞出的留白。
长安十二时辰
沉浸式街区里,春被切成二十四段。
我在“上元灯会”场景里,看见一位“李白”举杯邀月,月是人造的,但酒是真酒。
我与他碰杯,他念:“长安春色归,先入青门道。”
我接:“我辈岂是蓬蒿人,来,干!”
曲江池
曲江池的春,是霓虹色的。
夜幕降临,水幕电影开始,杨贵妃的影像从水中升起,裙摆滴着光。
我身旁的小男孩问妈妈:“杨贵妃是不是住在水里?”
妈妈答:“她住在诗里。”
奥体中心
奥体中心的春,是金属味的。
钢结构的“石榴花”绽放在灞河之畔,像未来写给过去的一封情书。
我带孩子去看演唱会,舞台灯光扫过人群,像扫过一片移动的银河。
孩子说:“爸爸,这地方好像太空。”
我说:“这是长安的太空。”
我想我会在青龙寺的樱花树下,摆一张小木桌,泡一壶陕青茶。
桌上放一本我未写完的《长安春笔记》,翻到最后一页,写着:
“亲爱的老赵:
你记得1982年的春吗?那时你刚调到西安,住在南稍门,每天骑二八大杠上班,车把上挂着塑料袋,袋里装着两个肉夹馍。
你记得1993年的春吗?你带女朋友(后来的妻子)去兴庆公园划船,船翻了,你俩在湖里大笑,笑得像两个唐朝的孩子。
你记得2008年的春吗?你抱着刚出生的儿子,在城墙上拍了一张合影,背景是朦胧的迎春花。
你记得2025年的这个春吗?你写完这篇《长安春色赋》,在永宁门城楼下,仰头看见一只灰喜鹊,翅尖划破了薄金色的晨雾……
如今你八十三,牙掉光了,但还能喝粥。你要记得:
长安的春,不在花里,不在风里,在你心里。
只要心里还装着一朵杏花,长安就永远是你的长安。”
长安的春,没有尾声。
它像一条河,流过周秦汉唐,流过我,流过你,流过每一个在地铁二号线低头刷手机的人。
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突然抬头对你笑:
嘿,我在这里。
在含光门早市的一枚韭菜盒子里,在钟楼地下通道的一阵萨克斯风里,在大唐不夜城的一面红墙下,在奥体中心的一声欢呼里。
它说:
“我是长安,我是春,我是你,我在这里。”


图片来自网络
作者照片
作者简介
王侠,北京老三届知青,系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,西安市未央区作家协会会员,山东鲁南作家编辑部特约作家,青年作家网会员作家。曾在全国各地人民日报(人民号)、解放军报、央视传媒、工人日报、中华魂网、馨语随笔、人民创作、长安文学(专栏)、陕西渭水之光、陕西灞水两岸、鲁南文学编辑部、BBEF艺苑声情传媒、山东作家、美文杂谈、诗意文韵、中国知青网等省部级以上一百余家媒体与平台上发表过文章,诗歌,小说,剧本,散文,科幻作品,歌词等。文学指导老师为陈荒煤、曹谷溪。中国电影刋授学院文学专业毕业,院长陈荒煤。曾参加山东青岛海军司令部进修班学习,陈荒煤主讲:有感而发。曾经在陕北(甘泉)插队一年零五个月,曾参加过大量知青慈善工作,社会教育活动,曾受到周总理接见,曾经荣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;荣获中华魂网“我的延安情”征文二等奖;曾被央视特邀海南三亚旅游并拍片。十八岁之前也曾经在北京司家坑小学,校场口中学就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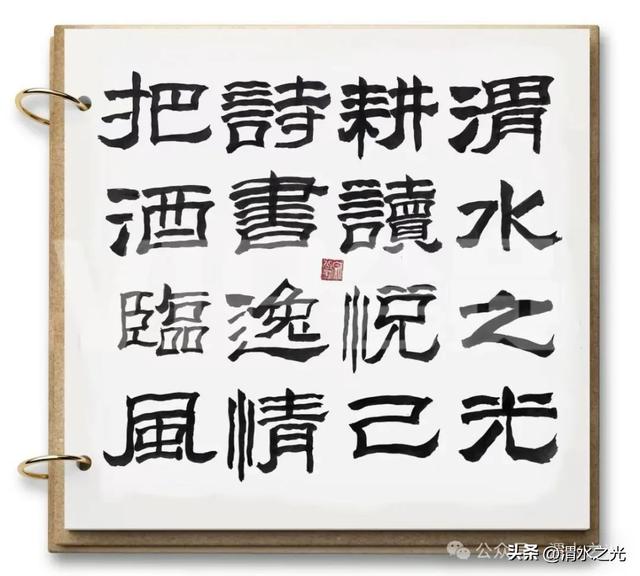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