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到过惠州之前,通过书本及网上的资料介绍,我对它的印象总绕着“半城山色半城湖”的朦胧诗意。总想着它该是座被山水裹着的城,西湖该有苏堤那样的柔婉,东江该泛着温润的波光。还念着它的梅菜扣肉,该是咸香渗进肌理的家常味,仿佛能闻见老灶蒸出的香气。也猜它该有慢节奏的生活,老街巷里藏着岭南特有的骑楼,风里都飘着几分闲适。
这几年一直都想去惠州走走,却因为这样子或者那样子的原因没有动——有时是工作突然堆起,有时是计划被琐事打乱。尽管从广州到惠州的城轨早已开通,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近在咫尺,那份向往还是一次次被搁置。直到这个暑假,终于把繁杂事暂放一旁,才算真正抽空成行,圆了这桩惦记许久的心愿。在惠州小住了一周,才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太多惊喜是书本及网上没有提到,只能用心去体会的……
刚出城际轨道站,惠州西湖便撞入眼帘,瞬间让人读懂这座城的奇妙——3.13平方公里的澄澈湖域,竟与281.4公里的蔚蓝海岸线在此共生。苏东坡笔下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岭南风情,与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楼宇相映成趣,古意与新潮在此交融得恰到好处。
租一辆单车沿湖而行,湿润的湖风裹着草木的清香扑在脸上,沁人心脾。这方湖水的故事要从东晋讲起,那时它还叫“丰湖”,因湖心丰山得名;直到北宋苏东坡谪居于此,才为它定名“西湖”,还亲手筑就苏堤、修起西新桥。往后千年流转,至20世纪90年代,终于酿成“六湖九桥十八景”的盛景,每一帧都是这座城的千年密码。
更令人称奇的是,一面是西湖的粼粼涟漪,一面是双月湾的滚滚浪花,281.4公里海岸线与湖景同处一隅。若初中时那位严谨的地理老师泉下有知,怕是要重新提笔,将惠州列为“山水城市”最鲜活的教科书案例。
站在合江楼遗址的楼顶上,望着惠城的全景,我突然就懂了:为啥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会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——住在这么舒服的地方,多吃点甜荔枝才够劲儿啊!
惠州现在还留着20处苏东坡的痕迹,像嘉祐寺、罗浮山、西湖这些都算。当年苏东坡甚至想在惠州白鹤峰定居养老,现在那儿改成了“惠州苏东坡祠”,成了大家纪念他的地方。九百年过去,他当年住的房子早就没了,只剩老井、古树还在,默默看着人世间的变化……唯那道东坡先生特别有缘分的梅菜扣肉,现在早成了惠州的招牌菜,一提惠州美食就想到它。
在广州的时候,我早餐总是随便吃两口就往公司赶。可到了惠州,我也学着当地人,把“叹早茶”过成了慢悠悠的事儿。凌晨五点的水东街,茶楼里的蒸屉冒着热气,我找个角落坐下,慢慢品一盅茶、吃两碟点心,别提多惬意了。
走在惠州的街头巷尾,常常能碰到一种叫“阿嬷叫”的传统小吃。“阿嬷叫”是惠州地道的传统小吃,妥妥的客家菜系代表,它的由来和客家文化紧紧绑在一起。过去客家人称呼父母,常说“阿伯”“阿姆”,这种叫法源自旧时的客家风俗——特意用略带疏离感的称谓,来凸显传统宗族里“长幼有序”的规矩。后来时代变了,“阿伯”“阿姆”慢慢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这类通用称呼替代,但“阿嬷叫”这类带着方言味儿的小吃名却留了下来,成了能勾起乡愁、代表惠州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。
黄昏在东江沙公园漫步,晚风轻拂时,忽然想起《追光的日子》曾在此取景——剧中惠州的自然风光、历史底蕴与现代都市感,此刻都真切铺在眼前。
入夜后站在鹅城大桥,两岸灯光映得江面波光粼粼,恍惚间竟有些失神。想起“鹅城”的由来:相传曾有仙人骑木鹅北来,被惠州美景留住,木鹅化作飞鹅岭卧于西湖畔,这地名便流传至今。直到江风裹着淡淡咸腥味吹来,才将人拉回现实。
临离开惠州那天,我拎着本地朋友送的特产——装得满满当当的惠州梅菜,还有一坛醇厚的东江糯米酒,沉甸甸的都是心意。
以前总在广州奔波,以为岭南是快节奏的代名词;直到来了惠州,才真正懂了“岭南者,江海之交”的意思——这里有西湖的柔、东江的润,还有海岸线的阔,把山水的慢与生活的闲揉得恰到好处。
心里已经盘算好下次再来:一定要记得带双透气的鞋子,好沿着苏堤慢慢走;更要彻底放空心情,跟着苏东坡当年的足迹逛一逛。或许到了夜晚,还能对着同一轮月色,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悠然心境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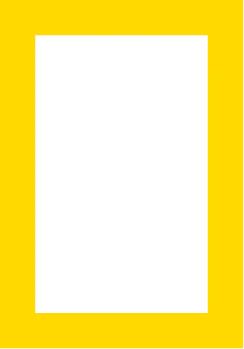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